第四节 曹溪的直指见性
「凡言禅皆本曹溪」,这是慧能去世一百年的禅门实况。到底曹溪禅凭什么有这样大的力量呢!
见性成佛
牛头宗说:「道本虚空」,「无心合道」。东山宗说:「即心是佛」,「心净成佛」。慧能继承了东山法门,不但说「心即是佛」,而更说「见性成佛」。神会说:「直了见性」。无住说:「直指心地法门」。黄檗说:「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」。所以曹溪禅的特色,是「直了」,「直指」;学者是「直入」,「顿入」。
曹溪门下的四家,对于「见性」,有从现实的心念中,以「无念」而顿入的;有从见闻觉知,语默动静中去顿入的。这就是宗密所说的「直显心性宗」,有此二家了。这二家的差别,可以从《坛经》的组成部分而理解出来。《坛经》的主体──大梵寺说法,是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,授无相戒」。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」,首先揭示了「菩提般若之智,世人本自有之」。于是立「定慧不二」;「无相为体,无住为本,无念为宗」;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,顿悟见性」。这是依经说的「般若」,「定慧」,「三昧」等而发明见性的。开示本性的「念念不住」,修「于自念上离境,不于法上念生」的无念法门。神会与无住所弘传的,重于「无念」,虽多少倾向遮遣,大体来说,是与这部分相应的。「授无相戒」部分,直示众生身心中,自性佛,自性三宝,自性忏,自性自度等。佛不在外求的意趣,格外明显。而答释疑问的:功德在法身,净土在自心,也与此相契合。这部分,可通于神会,而更近于洪州(及石头)的风格。这二部分,《坛经》(炖煌本)以「自性」为主题而贯彻一切,直显自性,见性成佛。现存的炖煌本,是荷泽门下的「坛经传宗」本。但只是插入一些与「传宗」有关的部分,而对所依据的底本──「南方宗旨」,并没有什么修改,所以现存的炖煌本,保留了「南方宗旨」的特色。上面说,神会所传的禅法,与「说摩词般若波罗蜜法」相近,但神会说「佛性」,「本性」,不用「自性」一词。在有关神会的作品中,没有「自性变化」说,也没有「形神对立」说。以「自性」为主题来阐明一切,是「南方宗旨」。神会所传的,应近于《坛经》的原始本。南岳与青原二系的兴起,得力于道一、希迁──慧能的再传,比神会迟一些。道一(与希迁)所传的,接近「南方宗旨」。慧忠晚年直斥:「聚却三五百众,目视云汉,云是南方宗旨」,可能指道一与希迁呢!但「南方宗旨」,决不是新起的,只是强调的表示出来,文句有过润饰增补而已。
慧能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」,当然是继承道信以来的禅门,是「不念佛,不看心,不看净」的一流。慧能在即心是佛(东山传统)的基石上,树立起「见性成佛」的禅,这是融合了南方盛行的《大般涅槃经》的佛性说。《大般涅槃经》,在现存北宗的部分著作中,也有引述,但没有重视。《涅槃经》的佛性,是如来藏的别名;但不是《楞伽经》的「无我如来之藏」,而是「我者即是如来藏义」,如《大般涅槃经》卷八(大正一二.六四八中)说:
「我者,即是如来藏义。一切众生悉有佛性,即是我义。如是我义,从本已来,常为无量烦恼所覆,是故众生不能得见」。
「佛性」,就是「我」,「如来藏」。如来藏原是为了「摄引计我诸外道故」而说的,形式上与外道的神我(常住不变,清净自在,周遍,离相等)相近,所以《楞伽经》要加以抉择,说是「无我如来之藏」。《涅槃经》解说为「如来藏即是我」,当然内容与外道不会完全相同,而到底易于混淆了。如来藏,我,佛性,不但是小乘,菩萨也不容易明见,如《大般涅槃经》卷八(大正一二.六五二下)说:
「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,乃至十住,犹未能见佛性。如来既说,即便少见」。
能究竟圆满明见佛性的,是佛,也如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二八(大正一二.七九二下)说:
「诸佛世尊,定慧等故,明见佛性,了了无碍」。
惟有佛能了了见佛性,明见佛性就是佛,所以梁代(天监中卒,五○二──五一九)僧亮(或作法亮)说「见性成佛」(大正三七.四九○下)。在这里,发见了「定慧等」与「见性成佛」的一定关系,也就是找到了《坛经》的「定慧不二」,「见性成佛」的来源。所以,达摩的「真性」禅,是《楞伽经》的如来藏说。道信以《楞伽经》的「佛心」,融合于《文殊说般若经》的「念佛心是佛」。到了曹溪慧能,更融合了盛行南方的《大般涅槃经》的「佛性」──「见性成佛」。内涵更广大了,而实质还是一脉相传的如来藏说。不过曹溪禅融合了「佛性」(即是「我」),更通俗,更简易,更适合多数人心,更富于「真我」的特色。
神会所传的「见性成佛」,是「见佛性」,「见本性」,如炖煌本那样的「见自性」,是没有的。所以以「自性」为主题的,推断为「南方宗旨」。如《坛经》(大正四八.三三九中)说:
「不思量,性即空寂,思量即是变化。……自性变化甚明,迷人自不知见」。
「自性」本来空寂(本净),而能变化一切。为什么会变化?由于「思量」;思量,自性就起变化了。「自性」,「自性(起)变化」,这是禅者本著自心的经验而说,还是有所(经说,论说)承受呢!也许受到「数论」的影响;「数论」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的一派。依「数论」说:「自性」(罗什译为世性。约起用说,名为「胜性」。约微妙不易知说,名为「冥性」)为生起一切的根元。「自性」为什么「变异」而起一切?「数论」说:「我是思」。由于我思,所以自性就变异而现起一切。这与「性即空寂,思量即是变化」,「自性变化」,不是非常类似的吗?陈真谛在南方传译的《金七十论》,就叙述这「变,自性所作故」(大正五四.一二四五下)的思想。论上还说:「如是我者,见自性故,即得解脱」(大正五四.一二五○中)。当然,「数论」与「南方宗旨」,决不是完全相同的。但对因思量而自性变化一切来说,不能说没有间接的关系。「自性」,或译为「冥性」,中国佛学者,早就指出:老子的「杳杳冥冥,其中有精;恍恍惚惚,其中有物」,从「道」而生一切,与「数论」的「冥性」说相近。所以「南方宗旨」的「自性」变化一切说,对未来的融「道」于禅,的确是从旁打开了方便之门。这些,是与曹溪本旨无关。
直指心传
曹溪的禅风,不只是「见性成佛」,而且是「直指」,「直示」,「顿入」,「直入」的。洪州(石头)门下,从见闻觉知、动静语默中去悟入;神会(无住)门下,从现前心念,以「无念」而悟入。这二大流,宗密统称之为「直显心性宗」。这一「直显心性」的曹溪禅,不是新起的,是东山门下所传的:教外别有宗──不立文字的,顿入法界的,以心传心的达摩禅。在第二章中,已有所说明。有关「意传」,「不立文字」,「顿入法界」,再引《法如行状》(金石续编卷六)如下:
「师(弘忍)默辨先机,即授其道,开佛密意,顿入一乘」。
「天竺相承,本无文字。入此门者,唯意相传」。
「唯以一法,能令圣凡同入决定。……众皆屈申臂顷,便得本心。师以一印之法,密印于众意。世界不现,则是法界,如空中月影,出现应度者心」。
法如是慧能同学,死于永昌元年(六八九,慧能那年五十二岁)。行状说到「唯意相传」,就是以心传心。「密意」与「密印」,也就是「一法」与「一印」。这里面,有三个问题:1.做师长的要善识弟子的根器,做弟子的要有入道的可能。2.如弟子确是法器,那就授法。行状说「一法」,「开佛密意」,但「一法」与「密意」到底是什么?据《传法宝纪》说:「密以方便开发,顿令其心直入法界」。在「密以方便开发」下,注说:
「其方便开发,皆师资密用,故无所形言」。
这是密用开发,是没有语言表示的。慧能的另一同学老安,以「密作用」开发坦然与怀让,密作用就是「目开合」,所以「密意」,「密用」,只是扬眉瞬目,转身回头,这一类身心的活动。这种动作,是暗示的,称为「意导」,「密意」。3.弟子受到师长「密意」的启发,机教相应,「其心顿入法界」,也就是「便得本心」。这本为师长自己的悟境,一经密用启发,弟子心中也就现起同样的悟境。《行状》所说「世界不现,则是法界,如空中月影,出现应度者心」,就是表示这一事实。这可说「以心传心」的,张说《大通禅师碑》(全唐文卷二三一)说:
「如来有意传妙道,力持至德,万劫而遥付法印,一念而顿授法身」。
「意传妙道」,就是「心传」。在「密意」开发,「顿入法界」的过程中,有师长的加持力(「力持至德」),好像师长将自己心中的证觉内容,投入弟子心中一样。这是语言以外的「心传」,在原始佛教中,称为「转法轮」。法是菩提,从佛(或师长)的自证心中,转入弟子心中,称为「得净法眼」。这一师资道合而直入法界,就是佛法的根本事实。
东山门下的禅,是有层次的。一般是「念佛名,令净心」。如学者有所领会,「密来自呈,当理与法」。授与的法,一般是不知道的,也不轻易向人说的,这就是「密以方便开发」的「密意」,「密印」。这在东山门下,得到的并不太多。神秀所传的,「以方便显」(第二开智慧门,有深方便),重于念佛、看净,这所以《传法宝纪》的作者──杜朏,要慨叹不已了。慧能在曹溪开法,不用念佛、净心等方便,而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,受无相戒」,直捷了当的指出:「众生本性念念不住」;「性起念,虽即见闻觉知,不染万境而常自在」,要学者直从自己身心去悟入自性──见性。这虽还是言说的,而到达了言说的边缘(如文殊以无言说来说入不二法门)。这是将东山门下的密授公开了(法如也有此作风)。慧能是直指直示,弟子是直了直入(这与顿渐有关)。凭慧能自身的深彻悟入,善识根机,要学者直下去顿见真如本性,禅风是焕然一新。到这里,达摩禅经历二度的发展:达摩传来的如来藏禅,本是少数人的修学,「领宗得意」是不容易多得的。道信与弘忍,在「一行三昧」的融合下,念佛,长坐,使门庭广大起来,引入甚深的法门。但东山的「法门大启」,不免流于「看心,看净,不动,不起」的方便。到慧能,将楞伽如来藏禅的核心,在普遍化的基础上,不拘于方便,而直捷的,简易的弘阐起来,这就是《坛经》所说的「大乘顿教」。
曹溪慧能不用「念佛」、「看心」等方便,直示「本有菩提般若之智」,以「无念为宗」,要人从自己身心去「见性成佛」。「无念」的解说为:「无者无何事?念者念何物」──神会这样说,洪州门下的《坛经》也这样说。炖煌本肯定自性起用的「念」,所以说「念者何物」,这是「南方宗旨」。《坛经》要人从现前身心中,众生本性的念念不住中去见性。虽说「性在王在」,以「自性」为生命的当体;什么是「性」,虽似乎呼之欲出,但始终没有明白点出「性在作用」。洪州门下所传的「性在作用」,与南阳慧忠所见的南方禅客相合。这是曹溪门下,更明白的,更直捷的,用来接引学人了!「识者知是佛性,不识唤作精魂」(神我);神我与佛性,洪州下是看作同一事实的(只是识与不识的差别)。的确,印度另一大学派「胜论」:「以出入息、视、眴、寿命等相故,则知有神」(大正三○.一七○下)。「胜论」也是以呼吸、视眴(瞬目等)证明是有我的。原始的如来藏说,从达摩到曹溪门下,是这样的公开,简易,直捷。人人有佛性,见性成佛;也就是人人有我,见我得解脱。这对一般人来说,这实在是简易、直捷不过,容易为人所接受、所体验的。这样的简易、直捷,难怪「凡言禅者皆本曹溪」了。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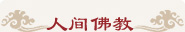

 川公网安备 51118102000121号
川公网安备 51118102000121号